你有没有想过,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争吵,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“戏”?
读罗伟章的《戏台》时,我总觉得他像一位坐在茶楼里的老朋友,用略带荒诞的语气,讲着一个让你笑中带泪的故事。他说:“两口子吵十年,和吵半个世纪实在没什么区别。” 可旁人反驳:“孩子长到十岁,还是个孩子;长到五十,你想想!” 你看,连吵架的时间尺度,都能被罗伟章写成一场哲学辩论。
一、假戏开场,真情暴露
故事从一场荒诞的“家庭演出”开始:表哥纪军约“我”喝茶,请求“我”配合演一出争夺房产的大戏,只为让争吵了一辈子的父母“团结起来”。理由是:“他们这时候,结成了利益同盟,心心相印,携手争斗,并因此和谐了、幸福了,也年轻了、精神了。” 可戏台搭好,演员却失控了——亲情在利益面前薄如纸片,假戏真做的争夺让两家人再不相聚。
罗伟章笔下没有夸张的台词,只有日常的细碎片段。比如姨母“从少女到人妇,再到母亲,她与这座城市割裂了,许许多多的故事,并不为她讲述,她更成不了主角”。一句话道尽了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无力感。
二、时代剪影,人性实验室
这场“戏”的背后,是罗伟章对历史的追问。姨母曾是穿裙子的城市知青,嫁到农村后“没再穿过裙子”,直到返城后挂着围裙卖炒干货,围裙上的花“一朵一朵凋谢”。而姨父的手“只沾牲畜的血”,却用克扣配种牛饲料的方式养活家人。他们的婚姻嵌着时代的疤痕:
“她穿着裙子进入农村,是个城市人;
她挂着围裙守在城市,是个农村人。”
罗伟章不评判对错,只平静地呈现:人性的复杂,往往藏在沉默里。他说:“有时候,沉默是金,但更多时候,沉默是石头。”
三、每个人都是戏台上的角儿
小说里最扎心的,是“看戏人”终成“戏中人”。“我”原本是表哥计划的旁观者,却不知不觉被卷入家庭纠葛;父母一辈在房产争夺中暴露了隐藏的私心;而表哥自己,一个“生活失意的小人物”,试图用一场戏治愈父母,最终却让全家陷入更深的隔阂。
这种荒诞感,恰如现实生活的隐喻:我们总想导演人生,却常被命运反噬。罗伟章写道:“这是他的界线意识,也是他的反界线意识。” 人与人的关系,本就是在界限与越界之间摇摆。
四、藏在台词里的生命哲思
罗伟章的文字像一把钝刀,剖开生活表层,让你看清内里的脉络。比如:
- “他万万想不到这种拯救也是伤害。”——好心办坏事,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。
- “所谓孤单,是因为对别人有依赖心,依赖心消除,孤单感也就自动解体。”——这句话简直是现代人孤独症的解药。
他写婚姻的疲惫,写亲情的算计,却始终带着悲悯。正如他所说:“从更深广的人的意义上,给自己定义。”
五、戏终人散,思考未止
合上书时,我想起罗伟章在创作谈中的追问:那对老夫妻为何突然精神抖擞?答案或许是:人需要共同的“敌人”才能团结,需要“演戏”才能靠近。但假戏演久了,真假难辨,最终留下的只有“我们两家无非是散了而已”的怅然。
《戏台》的惊艳之处,在于它用一地鸡毛搭建了一座人性的神圣殿堂。它告诉你:生活没有剧本,但每一次清醒的选择,都是在为自己搭建真正的“戏台”。
作者:家禾 丨 文章链接:https://www.duanjiahe.com/4235.htm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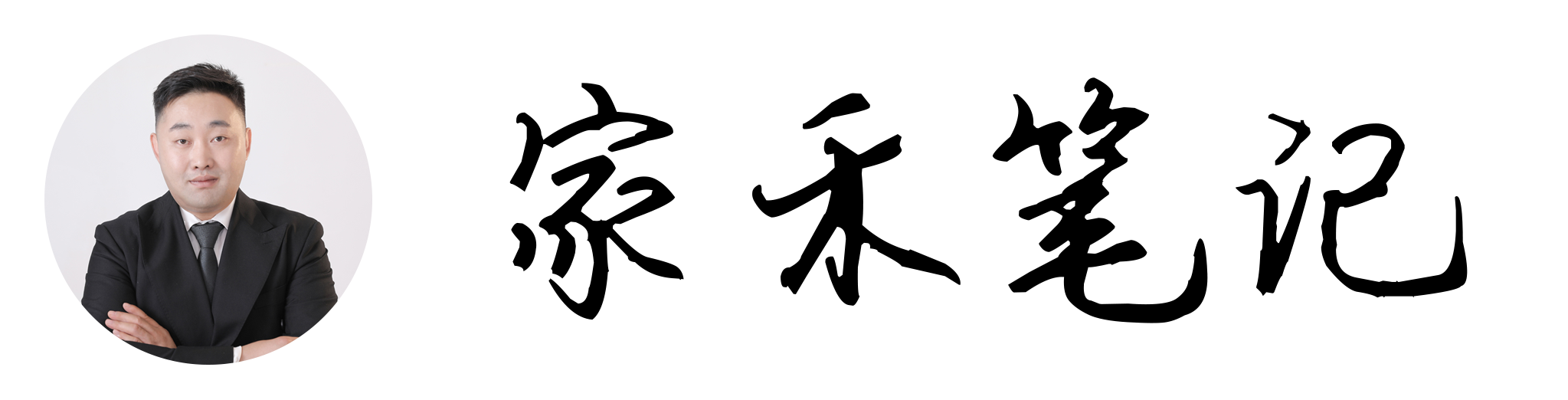
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